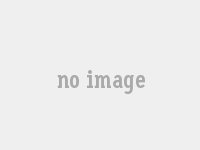儿童文学同样可以鞭挞假丑恶,甚至可以表现残酷的内容,但是不能太过分。你就是写恶也是为了凸显善的珍贵,你即使写冷酷也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温暖的。
记 者:您一直以来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,但近几年写了多部儿童小说,为什么在创作成熟期转向儿童文学创作?
赵丽宏: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每个作家都有童年,童年的生活,也许是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,会影响人的一生。在自己的创作中写童年的记忆,写和孩子们的生活有关的故事,这是每个作家都会做的事情。有评论家说我写儿童长篇是一次写作的转型,我不这么认为,写童年生活,为孩子写作,其实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么做。我的不少文章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,这使我和孩子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。尽管这些收入课本的文章并不是专为孩子们所写,更没有想到会收入语文课本,但这些文字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孩子的读物。我经常收到来自中小学的读者反馈,使我从中了解他们的想法,这也时常提醒我:在我的读者中,有很多孩子,决不能忽视他们。
这些年,我也一直关心青少年的阅读状况。孩子们从小是否能亲近文字,是否有高质量的好书陪伴他们的成长,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然而现状并不让人乐观,儿童读物铺天盖地,良莠不齐,小读者是盲目的,他们可以用来读课外书的时间不多,如果不能选择优质读物,后果堪忧。在上世纪90年代初,我曾经花两年时间,编过一套中小学生课外读物,把我从小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很多经典名篇汇集在一起,我想这样的读物可以让孩子认识文学的魅力,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。书出来,很多人说好,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。而且,我发现同类的书铺天盖地,良莠不齐。我发现,在儿童读物中,引进版图书占据了极大的比重,如果外国童书在中国一统天下,那显然是不正常的。中国的作家们不能听之任之,应该有所作为。那时我就动过写儿童小说的念头,但写作散文和诗歌,使我没有时间精力心有旁骛。不过,那个念头一直没有消失。6年前,在好朋友的鼓动下,我写了儿童长篇小说《童年河》,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很明确地为孩子写的作品。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影响出乎意料,小说被孩子们接受,成人读者也接受,从中读到了他们经历过的岁月沧桑。此后,我又写了《渔童》。《黑木头》是我的第三本儿童长篇。

记 者:是什么样的契机或灵感促使您创作了《黑木头》这部关于“流浪狗”的作品?
赵丽宏:是生活中的遭遇使我得到了创作的灵感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确实遇到了和黑木头命运相似的一条小狗,这条小狗感动了我,给了我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和动力。
大概是在4年前,在离我居所不远的一个中学里,人们发现了一条流浪狗,它每天晚上在校门里面出现,远远地注视着从校门口经过的人。人们给它送食物,大声招呼它,但它始终和人保持着距离,不让任何人靠近它。我也是关注它的人之一。这条小狗孤独、沉默,不愿意接近人。我很好奇,想接近这条小狗,想了解它的过去,也想探知它如何在孤单中生活。但是我只能远远地观察它,每次走近它,它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而且,和它的相遇,都是在天黑以后。
还有几个过路人,和我一样关注这条小狗,好几个人每天晚上到学校门口来给它送食物。有一位中年女士,执著地设法想收养它,带它回家。小说中笼子和麻醉枪的故事就是那位女士的作为,我亲眼目睹,甚至亲身参与其过程。这条小狗以它的智慧和倔强,和关心着它的人周旋,没有一个人能接近它。这条小狗和人的对峙延续了整整两年,春夏秋冬、风雨霜雪,它总是以相同的姿态,等候在校门口。它默默地在黑暗中出现,然后幽灵一般消失。
我设法了解这条小狗的过去,想知道它为何如此孤僻多疑,如此不信任人类。得到的信息隐约而不完整,但是很确定的是,它曾经被人虐待,所以它拒绝有人接近它。我曾经很多次在街心花园和马路上和它单独相遇,我大声喊它,想和它交流,它只是回头看我一眼,每次都毫不犹豫地离开。这条小狗,是一个既让人惊奇又让人心疼的谜。
两年前,这条小狗突然消失,不知去向。我每天晚上经过这个中学门口,都会停下脚步,希望看到它,但它再也没有出现。我想,也许,它已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中孤独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的小说,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构思。在小说中,我给这条小狗取名“黑木头”,并以这个名字作为小说的题目。我在小说中写一条流浪狗的命运,也写人间的亲情和动物之间发生的冲突和契合,这是生灵和爱的故事,这样的故事,可以让现代人思索生命的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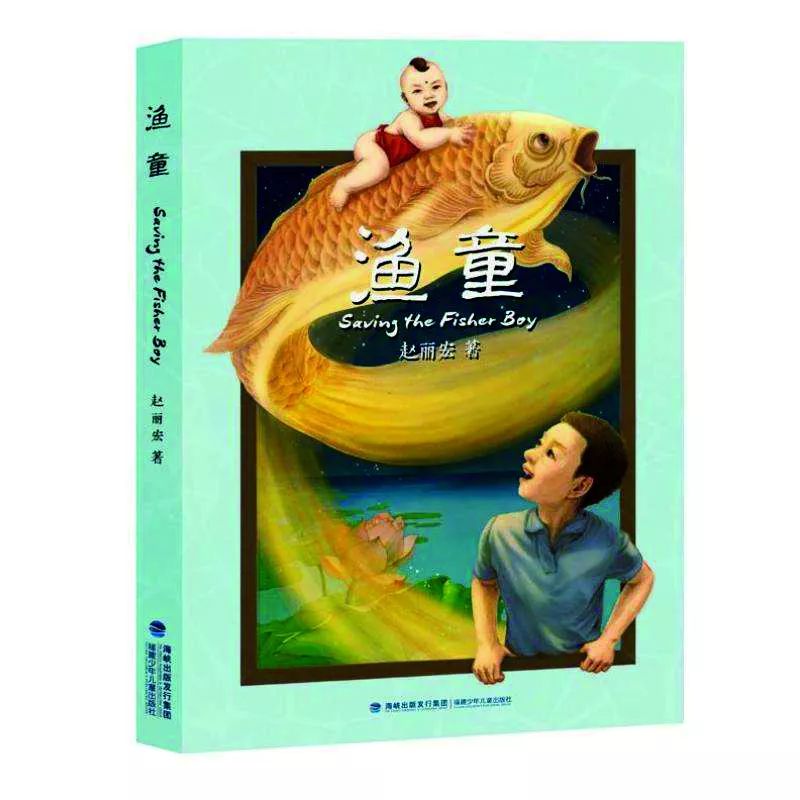

记 者:小说以流浪狗的名字“黑木头”命名,写了它被收养、被遗弃、再次被收养以及因为救主人而死去的经历,但其实故事中的众多人物对于黑木头的关爱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,通过这部小说,您想向孩子们传递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思考?
赵丽宏:作家张炜在读了《黑木头》后,写了这样的评语:“这是一条城市流浪狗的传奇故事,是悲喜交加、感人至深的心灵之歌。我在少年热泪闪烁的眸子中,读到了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仁慈与挚爱,还有不同生命之间丝丝相接的痛感与热望!一部救助书、一首惋叹诗,一条激越奔涌的爱之河流!”张炜的这段评语,被印在此书的封底,谢谢张炜,以简洁有力的文字,对小说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点评。小说写一条流浪狗的命运,它的孤独,它的倔强,它的坚忍,它和它周围环境顽强不屈的抗争,这其实也是生命的赞歌。生活中黑木头的原型,引起我很多思索。这些思索,在小说中没有什么议论,我希望用故事本身让读者得到启迪。人和自然,和世间的万类生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有着共生共荣的命运。对动物的同情、怜悯和关爱,其实也是人类对自身的尊重。我想表达,并且想告诉读者,我们应该关心动物,关心世间各种不同的生灵,但是更应该关心和爱的,是人,是自己的亲人,是周围的朋友,是所有需要关心的人。“让世界充满爱”,这爱,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爱。
记 者:小说中外婆的变化也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。外婆因为从小被狗咬过,对狗抱有偏见,特别是女儿和外孙对狗的关爱,又触动了外婆独居老人的孤独感;而最终是流浪狗黑木头陪伴外婆并救了外婆的性命。关于需要陪伴的老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细节,您写得很真实,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现实意义上的考虑?
赵丽宏:是的,外婆是小说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,可以说,黑木头的故事,从某种意义上是围绕着外婆展开的。最近这几十年,城市里宠物大量出现,养狗成为时尚,也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。狗是人类忠实的伴侣,很多生活中孤独的人,养一条小狗、养几只小猫,生活增添了乐趣,也驱散了孤独。有老人养一条狗伴老,给晚年生活带来乐趣,也有家庭因为宠物引发矛盾。宠物的大量出现,也产生了不少相应的社会现象和问题。如对宠物的过分溺爱,甚至“重狗轻人”,这成为很多人的担忧。我曾经亲耳听到有一个老人这样说:在家里,我不如那条被女儿和外孙宠爱的狗,真想变成一条狗。
在《黑木头》中,外婆对童童说:“我真希望变成一条小狗。”这是老人的无奈,也是老人对亲情的呼唤。我写《黑木头》,不仅是为孩子,也是为老人,为那些孤独的需要关爱的老人。这部小说,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个醒:决不能因关心宠物而轻慢了老人。小说中,对黑木头的关注和救援,与对外婆的关心和爱,始终交织在一起,这两条线索,既矛盾纠缠,又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,最后完全重合。童童一家和外婆之间的很多细节,可以说来自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儿子八九岁的时候,我曾经让他每天给我父亲打电话,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情就是拨通爷爷的电话,和他聊一会天。这样的祖孙通话持续了一年多,直到我父亲去世的前一天。我父亲告诉我,晚年最让他高兴的事情,就是每天孙子来电话和他聊天。我父亲已去世24年,父亲去世后,好强的母亲一直独居,坚持生活自理,还写日记。我不能天天去看母亲,但是经常给她打电话,近十多年来,给母亲打电话已经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,每天晚上九点半,是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间,没有接到我的电话,老人家无法入睡。不管走到哪里,哪怕到了地球另一边,我也要算好时差,准时打电话给她。我的母亲今年96岁了,我们母子间的通话,大概有五六千次了吧,这样的亲情通话,还会一直延续下去。在《黑木头》中,童童父亲让童童每天晚上给外婆打电话,这样的情节,确实是来源于生活。
记 者:小说中写童童想着黑木头时写道:“好像它的孤独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并不存在,在秋风中,它的孤独会被风吹散”,这种富于诗意的语言还有很多。我们都知道散文是特别讲究语言美的,您在写作儿童文学作品时也会刻意地锤炼语言吗?
赵丽宏:《黑木头》的语言延续了我以前的创作风格,并没有刻意的改变。有些人认为写小说只要客观叙述就可以,简洁明了,这是小说家应该追求的境界,风景描写或者抒情是赘笔,即便和人物故事有关,也没有必要写景抒情。这样的观点,也许不无道理,可以成就有些小说家的创作。但这样的观点有违我的看法,小说创作,也是文字的艺术,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文字来讲不同的故事。可以有巴尔扎克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,也可以有雨果和普鲁斯特的抒情风格。《黑木头》出现的一些景色和心情的描写,我觉得也是小说中人物心绪和情感的流露和反照。这样的文字,可以让读者的感觉和小说中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。小说中的写景抒情,其实也是叙事和情节的组成部分,并非赘笔。我写诗、写散文四五十年了,写小说时出现类似的语言,那是情不自禁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儿童小说用什么样的语言,用什么样的故事结构?是否要和我以前的创作做一个切割,用截然不同风格和方式来叙写?是否要俯下身子,装出孩子腔,以获取小读者的理解和欢心?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。我相信现在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悟性,真诚地面对他们,把他们当朋友,真实地、真诚地向他们讲述,把我感受到、思想到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他们,他们一定能理解,会感动,使我不至于白白耗费了心思和精力。诚如写了《夏洛的网》和《精灵鼠小弟》的E.B.怀特所言:“任何人若有意识地去写给小孩看的东西,那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你应该往深处写,而不是往浅处写。孩子的要求是很高的。他们是地球上最认真、最好奇、最热情、最有观察力、最敏感、最灵敏,也是最容易相处的读者。只要你创作态度是真实的,是无所畏惧的,是澄澈的,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东西。”
记 者:您近几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涉及到了不同题材,《童年河》写从农村到上海的孩子因为河结交伙伴的童年故事,有很浓厚的怀旧气息;《渔童》以自己的儿时回忆写出特定历史时代之痛,您觉得在小说题材上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,您是如何选择和处理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材的?
赵丽宏:我对儿童文学一直心怀敬意,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,用生动有趣的故事,不动声色、深入浅出地讲述人世的哲理,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,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。文学的题材和体例有时难以分界,儿童可以读成人题材的文学作品,成人也可以读儿童文学。真正优质的儿童文学,应该能让成人和孩子一起来读,它们一定是文学精品。前几年访问丹麦,我去了安徒生的故乡,参观他的故居,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散文《美人鱼和白岩》,在文中谈到对儿童文学的看法。我觉得安徒生童话就是最高级的儿童文学,它们表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,由浅入深,由此及彼,让读者产生美好深远的遐想和思索。这样的文字,孩子可以看,成人也可以看,可以从小一直读到老。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儿童文学,也是最高境界的文学。
我写的三部儿童长篇,反映的是三个不同的时代,《童年河》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,《渔童》是1966年前后,《黑木头》是当下的生活。从时代背景看,三部小说,越写越近。三部小说,内容不同,但基调是一致的,都是展现人性之美,展现人间的真和善。在写儿童长篇时,我的创作状态应该说是一如既往,依然用我自己个性的语言来写,不会刻意装出孩子腔。依然是用真诚的态度,力求准确真实,不过度夸张。写这几部小说时,我力求让自己在精神上回到童年时代,对小说中所涉及的任何事物,任何情景,都会想一想,在孩子的眼中,在孩子的心里,应该是怎么样的,而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,以一个自以为万事俱晓的聪明人的口气,来讲述故事。
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重要区分,就是叙述者的视角和心理,如果没有儿童澄澈的视角,没有儿童的鲜活的心态,那就不是儿童文学。儿童文学同样可以鞭挞假丑恶,甚至可以表现残酷的内容,但是不能太过分。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是写那些阴暗的、血腥的、可怕的事情,对孩子肯定会留下阴影。你就是写恶也是为了凸显善的珍贵,你即使写冷酷也应该让孩子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温暖的。
本文发表于《文艺报》2018年7月18日7版